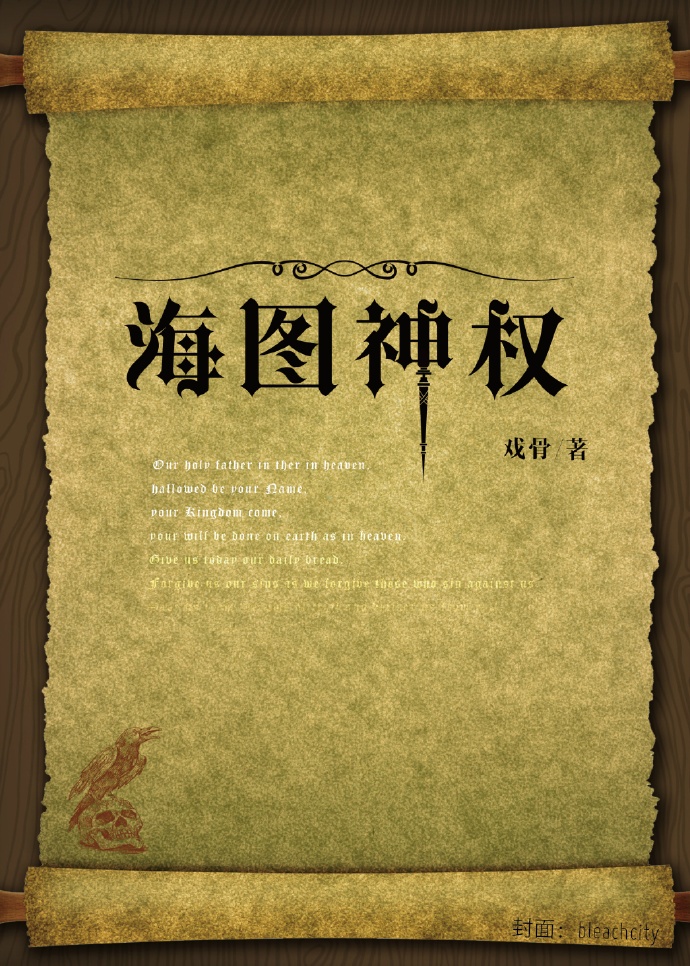那個倒黴的少年被一群蜂擁而上以為自己能走運射中酒杯的水手呼啦啦從身上碾壓過去,等他好不容易邊呸着嘴裡的灰邊爬起來的時候,面前已經被黑壓壓的人群擠占了全部的視線,隻得苦哈哈地排在隊伍的最末尾,等着前面那些不死心的先試過再說。
也偏偏他耳聰目明,竟然從人潮洶湧中還能聽見哈斯勒和依蘭達的對話,回頭疑惑地問了句,“科斯塔結?”
這一手登時讓依蘭達刮目相看,在海上,這種超凡脫俗的聽力可不多,有時候甚至還能起到提前預見風暴的作用。
要知道……是真有一部分人能聽見風暴将來的聲音的。
射箭這種東西可做不得假,大批人心懷惴惴祈禱老天開眼的上去,再愁眉苦臉一臉苦相的下來,倒不是沒人不死心還想去試試的,可依蘭達一開始就說了隻準嘗試一次,自然也就堵死了某些人企圖靠多次嘗試撞大運的想法。
當然也有人企圖幾個人一起射蒙混過關的,他們也都被托尼叉出去了。
一群人戰敗之後,自然有人開始起哄說這壓根沒人能做到,依蘭達作弊!
這就是純粹搗亂的了,自己肯定上不了船也要慫恿着一些沒長腦袋的也上不了船,一時間還真有些腦袋長包的開始咋呼了起來,場面一時間有些混亂。
這時,托尼默默的搭弓射箭一箭瞄準了酒杯射了個粉碎,于是傳這種謠言的也歇了。
什麼你說萬一真有人撞大運?要是真能有運氣爆表的人依蘭達也認了!
開玩笑,運氣在海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又不是沒有十項全能的水手反而被幹掉了而屁都不會的反而毫發無傷的,總而言之,隻要你能射中,就能上船!
比射箭的比較直觀,依蘭達那個酒杯周圍簡直被亂箭插成了灌木叢,幸虧那棵樹的方向不是什麼主幹道方向,一時間亂箭飛舞,連帶着從旁邊港口行駛過的船都遭了殃。
不時有憤怒的船長和水手揮舞着手臂大喊,“射你娘的射!你爸當時怎麼沒把你射牆上!”
然後再忙不疊低下頭,一根箭從耳邊晃晃悠悠地飛了過去,再軟綿綿的碰到船艙上,然後啪叽一下掉在了船長腳邊。
船長:“……”
在争先恐後比試射箭的這段時間,港口上簡直是鬼神莫近,但凡是靠近的都被那些自诩為說不定老天賞飯吃的給插成了刺猬。
可這當中也不全是渾水摸魚之輩,竟然還真有那麼十來個射中了酒杯的,這幾個幸運兒則在托尼的監督下成為了免試的幸運兒。
真要有能耐的,早就被各艘船招走了,真要說可能存在什麼别的船的探子,也就是在這群尖子裡頭,畢竟明擺着拿錢來砸的,又怎麼會招不到好苗子?
正當依蘭達打算一個個看看這些個她未來的班底的時候,一個彬彬有禮的男聲響了起來
“請問……我能試試這個水手結麼?”
這還是第一個說要來挑戰依蘭達的水手結的勇士,女海盜詫異之餘,回過頭卻看見了一張文質彬彬的根本不像是水手的白皙面孔。
女海盜狐疑地看了他片刻,這才回答道,“當然可以,可是……這裡是招水手。”
如果想要招文員隔壁阿爾蒂爾右轉走好。
“那就沒錯了,”男人笑了起來,“我就是來應征水手的,請讓我嘗試一下那個水手結可以嗎?”
“沒問題,”女海盜也沒指望他能完成,随手扔給他一段繩子,“你在半個小時之内打出來就算你過關。”
如果超出半個小時……呵呵連船都沉了就算打出花來恐怕也沒什麼必要了。
科斯塔結的難打程度從來都是喪心病狂,也正因為如此,依蘭達也沒太往心裡去,反正在場的估摸着都沒幾個人認識,也就準備去托尼那看看,可她才走過去沒一會,那個男聲又響了起來。
“我打好了,麻煩您看一下。”
依蘭達:噢打好了?什麼打好了?!
她下意識回過頭去,登時看見那個過分白皙的男人将一個再标準不過的科斯塔結拿在手中,“這樣可以麼?”
女海盜簡直吓了一跳,她走過去的時間最多也就六七分鐘,這男人看起來速度竟然比她都差不了多少。
“你就打好了?”
男人看了看手中,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是的……如果您不相信我還可以再打一次。”
“不必了,我看着他打的。”哈斯勒的聲音響了起來,剛才依蘭達去看熱鬧的時候他可是還看着這邊。
女海盜詫異了一會,可還是點了點頭,“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康德克萊芒。”男人有些局促,“我想請問一下,我……可以被錄取嗎?”
女海盜眯起了眼睛,“這樣吧,你把你的資料留下,你已經過了第一關,如果看了你的資料沒什麼問題的話,你就可以上船了。”
“那麼……是什麼時候呢?”康德更窘迫了。
“你很着急?”依蘭達有些詫異,“如果選好了人之後應該很快就會開船了。”
現在馬上就要進入風暴季,勒戈夫在塔比斯海灣估計也撐不了太久了。
“……是這樣的,”康德猶豫了好一會,“如果,如果你們選中了我,能先讓我預支工錢嗎?”
說完之後他似乎知道這也相當不妥,馬上補充道,“我可以幹很多髒活累活的!給我多安排幾個人的活計也沒關系!”
“你有什麼急需用錢的地方嗎?”依蘭達順着話頭問道,雖然這個康德看起來不像,但是水手很多都是爛賭鬼,她可不希望自己船上也招上這樣一個人,即便他看起來身手不錯也一樣。
要知道,一個賭債纏身的人可是什麼都做的出來的。
康德很顯然是個聰明人,看見依蘭達這麼問立馬就做出了解釋,“不不不您誤會了,我沒有賭博,也沒有欠債。”
“……是這樣的,我的妻子現在得了重病,需要錢買藥,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所以隻好請您預支。”
“她得了什麼病?”
康德張了張嘴,漲紅了臉,“我……我可以不說嗎?”
“你必須得說,”依蘭達淡淡道,“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船上有一個來曆不明的水手,在你一會要提交的資料裡也會說明這一點。”
這可不是她能施舍善心的時候,她的任何心慈手軟,都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作為一個船長,為自己的船員負責是最基本的條件。
康德沉默了許久,這才艱難地開了口,“是……納瓦拉的疫病。”
聽說是疫病,哈斯勒的臉色登時變得有些難看了起來,他掏出火石,當場就把剛才康德碰過的那根纜繩給燒掉了,半點情面都沒留。
“我們這裡不需要你。”
聽到這聲審判,康德的臉色登時變得灰敗了起來,過了好一會才低下頭,微微鞠了一躬,低聲道,“好的,我知道了。”
依蘭達的神色也不太好看,雖然她自己也剛從疫病中恢複不久,可也清楚納瓦拉的疫病究竟是一種怎樣可怕的東西。
可這康德實在是個好苗子,看起來有點太可惜了。
“别爛好心,”哈斯勒警告道,“疫病可不是什麼好對付的東西,他妻子生了病,現在看着他還挺健康,可萬一他把疫病帶上了船,那我們一船的人都要給他陪葬!”
“我知道。”依蘭達點了點頭,雖然可惜,可也在心中把此人的名字給劃掉了,誠然,她不是不能從居伊小少爺那再弄點防治的兩葉辛普瓦草,但是這并不是長久之計。
整艘船上的水手都會因為這樣一個人的存在而恐慌,哪怕是個好苗子,也不值得讓一艘剛剛建立起來的不穩定隊伍冒這樣的風險。
見依蘭達并沒有動心,哈斯勒這才點了點頭,“我知道他,康德的确是個好水手,人也信得過,之前也是在一艘商船上固定的水手長,可他這個人特别疼愛自己的妻子,遇到任何和妻子有關的事都是妻子優先,估計這次也是因為妻子生病所以被從原來的船上趕下來了。”
“原來是這樣。”依蘭達點了點頭,也沒太往心裡去。
可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巧合,誰又能知道,這個康德竟然在後來依然登上了她的船,還是以一種她沒想到的身份。
所以說,現實才是最佳的戲劇導演,時不時就會以各種突發事件糊你一熊臉。